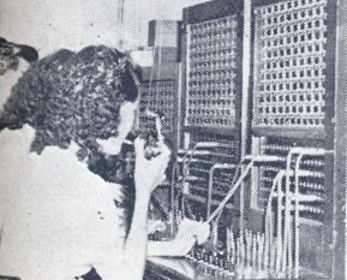本文摘自孟慶玲女士編輯之家族刊物《我們的報》。2024年1月26日在本站首次轉載。
文/楊嫌撰寫,滕淑芬編輯
蘇麗圓是我的同學,我們都是日治時代出生的台灣小孩。她是小學二年級轉到鳳山西國民學校(編注:今之鳳山國小)的,那是我們一生中所受的唯一的正規教育。當時她的名字叫做「蘇氏水金」,日本名是「金子」;我則是「楊氏嫌」,日本名是「陽子」。當時 女人的名字都要在姓下面加一個「氏」字。
遇見兒時同學
民國53年寒假,因為台北區的防洪工作由憲岳負責基隆河關渡出海口的拓寬工程,所以全家從屏東搬來台北。剛搬來的時候,住在和平東路陂心段,買菜要到成功新村的成功市場,這附近是軍眷區,有一次,我正提著菜籃走著,突然被一個甜膩膩的聲音吸引住了,轉頭一看,路旁正在逗弄小女孩的少婦,不就是「金子」嗎?「啊!金子桑!金子桑!」我怕失去這個機會,便立刻走過去叫她,金子桑很驚訝的眼神,似乎一時想不起來。

這也難怪她,我們自從昭和19年(民國33年)畢業以來,就沒有再見過面,整整二十年了。我趕快告訴她我是陽子――楊氏嫌,能夠在台北遇到同學,太令我高興了,想起從前當小學生的事,我們都還記得很清楚,講到有趣的地方,兩個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記得四年級的時候,班上有一位姓黃的同學,她的爸爸是我們學校的老師,後來他們改日本姓,她就叫作「本田尙子」。這位「本田」上課答題時,喜歡把頭歪一邊,講話又很扭捏做作的樣子,很討人厭。下課時,只要有本田在場,就會有同學推另外一個同學去撞她,碰到她的人就拍拍身上說:「細菌還給你。」 這樣鬧著玩。
班裡另外有一位同學叫黃氏仙鶴,鶴子她家開布行,常拿布、鉛筆、橡皮擦、大楷紙等來放我桌子抽屜裡,她說要給誰就由我來發。有同學來告訴我說:「本田說你是鶴子桑的大將呢!」她們跟我講這些,大概想要看我跟本田吵架吧?反正我本來就對她沒有好印象,經過別人的挑撥就更討厭她了。
被日本老師訓斥
我們級任老師大濱先生,是一位矮矮胖胖、皮膚黑黑的日本小姐,這位先生很和氣,有一次她請假,班上又鬧起來,本田叫她爸爸來,把李氏月娥一巴掌打得流鼻血,當時普通家庭的家長都不敢到學校去理論的。
第二天大濱先生來處理這事,她叫本田說出誰對她不和善,本田講一個,先生就叫一個,被叫到的就到講台上正座(跪坐)。哇!我也被叫到了!回頭看教室內,沒被叫到的只剩幾個人了。我也到講台上去正座了,講台上擠一大堆同學,每位同學嘴裡都唸唸有詞,大概在練習怎麼回答吧?糟糕,我腦筋裡空空地,不喜歡她是真的,可是並沒有直接衝突過啊!
詢問到我了,先生開口就問:「陽子桑怎麼和本田桑不和好呢?」我脫口說:「她說我是鶴子桑的大將啊!」當時先生的眼睛團團轉, 疑惑地說:「『大將』又不是什麼壞事。」先生這樣說,我只有低下頭不知說什麼好,後來先生又問:「你恨她嗎?」我搖搖頭。先生深深地嘆息,我就站到一邊去了。搞了半天都問完以後,先生把我們訓了一頓,叫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和她握握手。但事後看到她,大家仍然拍拍搓搓手,嘴裡還是說:「細菌還給你。」
與金子桑談起這件事,除了哈哈大笑外,她說那次她沒有被叫出去,可見得她人緣有多好!
記得同一年的「健康週」,大家做健康標語,我有兩則入選。那時候我們上課都用日文,兩則標語翻成中文,一則是「走呀走,邁開大步向前走」;另一則是「浴日光,細菌逃」。大濱先生告訴我說一個人一則就好,另外一則讓給別人。表揚的時候,我得的是「走呀走,邁開大步向前走」,「浴日光,細菌逃」的得獎者居然是「本田尙子」。她作的和我一樣啊!我後來想起大濱先生說「一則讓給別 人」,原來就是讓給她呀?
「阿母,女兒真對不起您!」
六年級那一年對我來說,最難過,心又亂,學校要再升學的同學留下來補課,我曾經哭著求過母親讓我再升學,但當時的家境絕對不可能,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、兩個妹妹,加上外婆和表妹,一家十三口全靠父親的小生意。雖然大姐、二 姐、哥哥有做事,但賺錢不多,看母親為難的樣子,現在想起來,真是於心不忍。「阿母,女兒真對不起您!」
那時的男先生(老師)是台灣人,本來姓陳,後改姓名叫佐野先生,會罵人。大家課上得不理想時,常大聲罵:「成績好的人不升學,一堆笨蛋卻要升學,怎麼能考得取? 」
我小學畢業能做什麼事呢?我心裡想,考紅十字會的看護去。
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,母親帶我到廟裡拜拜,祈求神明保佑我能找到好工作。昭和19年3月(民國33年)我小學畢業了,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很激烈,一天躲好幾次警報,躲在防空洞裡,要考紅十字會護士,該準備些什麼也不知道。
接錯線
一個禮拜了,鳥丸先生到家裡來找我,我們學校每年級男女各兩班,他是六年級另一女生班的先生,他把我和他班上的蔡氏嬌――日本名美雪,帶到鳳山郡役所――等於縣政府,介紹給財務主任武籐,是個日本人,也是我五年級時的先生的丈夫。
武藤主任讓我做電話交換台的交換手(電話總機的接線生),美雪桑是郡守室的給事(縣長室的工友)。那時代電話沒有像現在普遍,而我也從沒有聽過電話,本來的接線生寶貴桑教我怎麼接,然後就高升到文書系(股)去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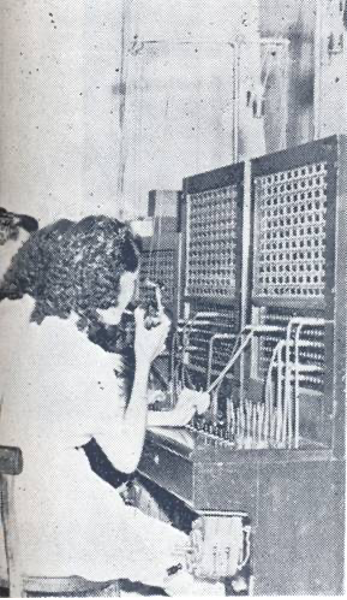
服務已三年的陳氏桑在哭,原因是空降下來的我,擋住了她的高升。結果我還不是一樣在哭,我哭的是頭腦不清,忙亂之下把工商系和農務系要往外面打的電話,接在一起讓他們講話。他們莫名其妙,跑到交換室來,本來大概要罵人的吧?看到我傻傻地愣在那裡,他們同時叫出:「怎麼?新交換手嘎?」
陳市桑人真好,她沒有恨我,還教我幫我。有空時,我和美雪桑去看鳥丸先生,他很關切地問我們:「習慣了沒有?社會不像學校那樣單純,要忍耐喔!」他那關切的聲音,到現在都還在我耳裡迴繞,鳥丸先生有教過文祥弟,他真是一位好先生,連調皮的學生也都說鳥丸先生是好先生,他關愛這一群台灣小孩,有過於台灣籍的先生。
我第一個月領到薪水,日圓多少錢記不清了,只記得薪水袋還擺在佛桌上拜拜呢!「好好地做下去,要等我回來喔!」那時候的我們年紀小不懂事,也沒有送給他幾句祝福的話。
大概上班有一年吧?代理武籐主任的陳曜勳桑,他是台灣客家人,他告訴我文書系有缺,要先升蔡氏嬌桑,她長得那麼高做工友不好看,要我等一等,是不是武籐主任交待的呢?還有已經做好幾年的人啊!我們兩人真是幸運兒!雖然升到她,叫我等一等,我也很滿足了。
我的電話交換台沒有了
大戰快進入尾聲了,記得昭和20年,民國34年的夏天,鳳山郡役所被飛機空襲給炸毀了。我的電話交換台也沒有了,當天我嚇哭了,隔天上班就聽到大家在傳說:「昨天交換手哭了。」辦公室搬到路那邊的公會堂,現在回想,躲入防空洞的那段日子,大家都說誰的耳朵又大又厚比較有福氣,就要跟他擠在一起,平常各人做各人的事,只有飛機來空襲時,大家躲進防空洞,說說笑笑,淡化恐懼感。
我的交換台沒有了,我就到財務系,幫日本人爺爺山之內桑,那時我覺得他很老,他辦各小學教職員的薪水,他誇獎我寫字漂亮,要油印時,刻鋼板、寫蠟紙都交給我做,還要填薪水請求書(單)、數鈔票、裝薪水袋,然後擺進特製的木箱,隨著車送到各學校。公會堂地勢高,風很大,我一坐下,沒有多久就發抖,我得瘧疾了。
剛開始是隔天發冷後發燒,後來一天內發冷發燒二次,是惡性瘧疾,我沒有辦法上班,總是得去報告一下,我去找財務主任,代理陳曜勳桑說我生病不能上班,他安慰我說沒有關係,好好養病什麼時候好了,再來上班。
我和病魔搏鬥了好幾個月,差一點送掉命,母親為我流不少眼淚,一家人被我搞得不得安寧,像二姊、小弟也患過瘧疾,都沒有像我那樣嚴重。
幾個月過去,日本早投降了,機關改變了,人事也變了,整個社會都變了,加上得瘧疾後,全身膚色像南瓜一樣黃,我到那裡去上班喲?美雪桑到鳳山醫院當護士,不知道是編過去的還是重新找的?而我是在光復後到青年軍所辦的「國語補習班」上了將近一年的課後,才因種種機緣進入「建設廳農田水利局鳳山工程處」,展開我全新的戰後生活,那都是後話了。
我現在再來介紹我的同學金子桑――蘇麗圓,我現在要改稱她為韓太太了,因為她丈夫姓韓,是裝甲部隊的軍官。我這位同學是多才多藝,在學校時,她的作文常被老師拿出來唸給大家聽,現在電腦學得嗄嗄叫,另外她還種蘭花盆栽,種得一屋子美極了。從民國53年的寒假至今,一直保持連繫,常常打打電話,我們曾在電話裡談到《我們的報》,我寄給她看,我問她要不要參加?她毫不吝嗇的把稿寄過來,她的這篇文章還登上報紙的呢!我很高興,能有共享回憶的老友,是人生難得的幸福!